引言
是书作者杨儒宾教授为华语世界资深优异的儒学研究专家,如名所见,《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论题涉及时空主要指向近世东亚,地域而外,就国史所历朝代,跨越了宋、元、明、清前后千年的间距。这一期间,与因跻身官学而一直当令的理学思潮发生争议的儒家学派,书中各章均有涉及,至少包括了中国的“气学”、日本的“古学”、韩国的“实学”。这些不同流派之间隔着相当遥远的时空,却针对共同的理念展开对勘,伊藤仁斋与朱子与戴震的相互发明,罗钦顺与贝原益轩的貌合神离,丁若镛与阮元的共襄相偶论,叶适与荻生徂徕的齐赞皇极学……事实面相的丰富令是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域均显得相当深远、宏阔。这些遍布东亚地区、延绵千载上下、彼此之间经常找不到相互影响的因子的异国度的儒者,关怀却意外的接近:他们一概反对广义的理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仿佛应了小程子解读《易经》那句名言,“一不独立,二则有文”,这种共同的焦点意识与理论意识,源自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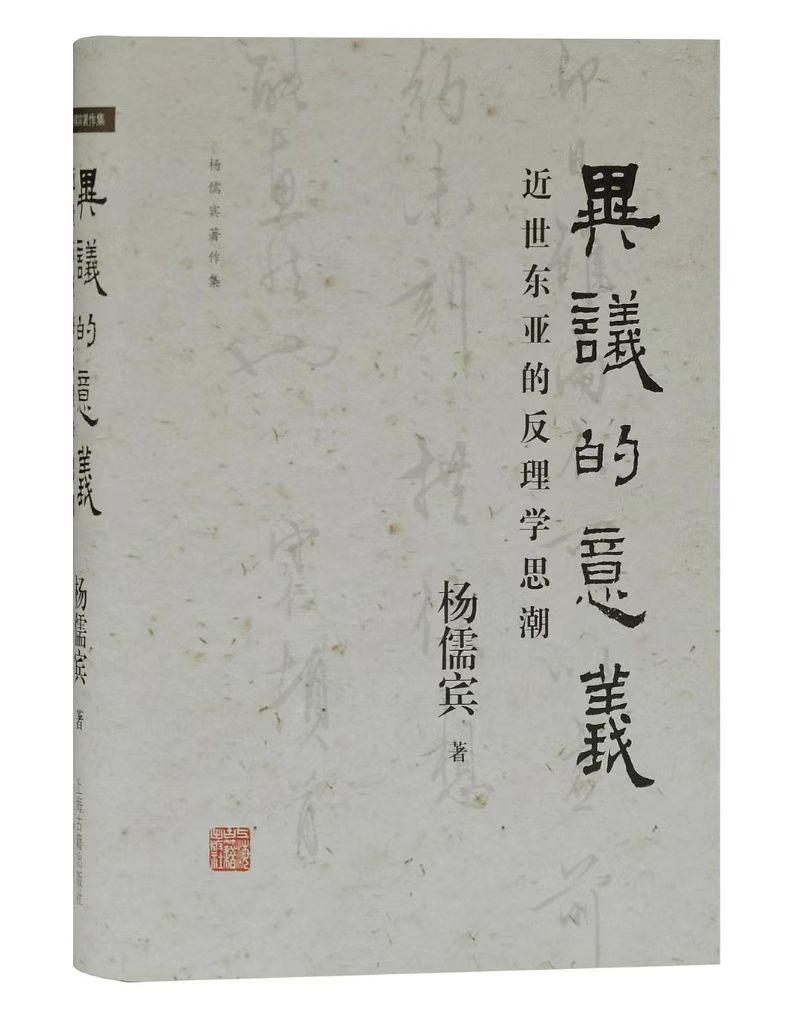
《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
反理学的思潮与理学并时而起,一路随行,究其根本,他们的反对,其实会指向一种影响东亚世界甚巨的思维模式:体用论。这一地区与这一时段固有的古典文献本身的丰沛性与歧义性,又足以支撑起如上这种“两面三道”的巨大争议。“两面三道”不是笔者的生造,而是这一异见的风潮的实相:如果说理学(含心学)与反理学的势不两立构成了现象的两面,相偶论与制度论对体用论的两面夹击,则构成了取径的三道。
对于崇尚所谓古学的儒学学者阵营,宋明儒者特别是朱子的理学诠释,是对古典的精深还是对古典的篡改,这怀疑来得并不突兀,自朱子学诞生之初,其实就没少过反对的声音,1200年确实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朱熹(1130-1200)于政治迫害风潮中安静的在黄坑走完他的一生,至于如何被平反、被肯定、被国师化,包括走出国门,远播日韩、北上蒙元,都是他的身后共业,哀荣与自体无关。但近世东亚的精神世界就此成了理学的东亚,确是不争的事实,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真正的儒家精神,是否只属于佛教进入中国之前的文化表现?这一提问,并非出自《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甚至亦非作者有意识的主轴关怀,却无形中建构了本书得以挺立的广阔的思想背景。那被近世东亚中、日、韩诸多学者不约而同抗言反对的理学,不正是受了佛教太多影响么?尽管对于宋明理学诸子自身,他们的定位恰恰是“出入佛老,然后反归六经”。自李翱(772-841)作《复性书》以下,儒者承荷的心灵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儒者不满于汉末以来儒学被局限在人伦教化的“方内”领域,灵魂之事却全为二氏包办。如何解码儒学经典中的“性命密码”,被饱受佛道包围的儒者视为义不容辞的天命所在。就此而言,理学的建立正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自我证明的体系,令儒学在自足的安身立命方面敞开精义。
但在反理学的阵营看来,理学家的一番作为,对佛学妥协太多,他们如果不是混入儒学队伍的异端,也是被佛教误导了方向,和对手过招拆招日久,严重被对手的武功污染,带上了太多对手的痕迹,最后竟然迷失了自家的本来面目了。
那么,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到底提供或发明了哪些此前不曾明朗、以至于此后经常被认为窃比佛老的儒学性格呢?义理的依据,确确实实是落实到了世界观与人性论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了,例如至少包括了如下几点:一,性具万理、人性本善的超越意;二,天理落于气质的现实意;三,学者通过主敬、穷理等路径以求“复性”的修养意(工夫论)。在这一“无限性的主体观”的设计之下,整体的儒学世界被彻底撼动了,例如圣人的典范由尧、舜、周、孔滑向孔、孟、颜、曾,“圣经”的范本由《五经》滑向《四书》。更关键的面相则是,自此以后,儒学的最高理想,“第一等的事业”变成了复性的事业。虽然同时并不废弃文化与人伦,但从明体达用的视角看来,“道不穷源”“落在气边”的判教却未免压了文化与人伦一头地。自此以后,经验的人性之外更深层的本性是否存有?任何的日常事件到底只是日常事件还是本体的外在显像?成为历代哲人不断争执的话题。在理学学者看来,这当然应该属于发露孤明、拨云见日,将此前埋藏于文献深处的真意发挥出来。但设若学者首先即不能接受以朱子学为代表的理学强力建构起来的世界观,则这一“洁净空阔的理世界”便随时面临被拆翻的命运。理学既可能是对潜存义理的朗显,也可能只是对儒学精神的扭曲,偏离了正宗的轨道。而在后世佛子看来,这一举措却又成了“入室盗法”。理学在近世东亚如日中天的同时,也往往都被两头为难。
反理学的儒者的处境和对手类似,如果要完成预期的反对任务,同样需要对儒学的主体论与形上学重新清理一番。定位为“古学”无疑是个很好的策略--日本儒者如伊藤仁斋(1627-1705)或荻生徂徕(1666-1728),确实也就是这么干的。追求经典的原始义的号召会显得很有说服力和号召力。而且如此之“古”显然不尽是时间意,更是价值意,依然暗含了对当下境的批判与对理想境的认定。将佛教进入中国这一节点作为临界点是常被使用的手段,佛教进入中国之前的原始儒家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儒家,反理学的儒者无一例外都是站在他们认为的“真儒”的立场上发言的。
杨儒宾教授经由“异议的意义”建构起来的近世东亚的反理学图景,特为精微之处,乃在:不仅凸显了相偶论对体用论的出击,更昭示了相偶论与体用论的一脉相承、相反相成;不仅凸显了气学对理学(含心学)的撼动,更昭示了气学中的先天型与后天型之名同实异、南辕北辙。

杨儒宾,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新竹)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著有《儒家身体观》《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从<五经>到<新五经>》《儒门内的庄子》等。译有《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孔子的乐论》《冥契主义与哲学》《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等。
一 体用论与相偶论
在广义的理学内部,朱熹生前即有不少论辩对手,例如鹅湖之会的“朱陆之争”,身后也有不少专事造反的儒门后劲,例如王阳明的格物不成而向内倒戈。但因为对于体用论这一思维方式的一致性,心学儒者与狭义的理学儒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只是对于如何“明体达用”的方式(工夫论)的不同,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体与用的具体关系的理解的不同,二者互相决定。
中国哲学概念中那些成系列的统一与杂多的对待名相,例如理-事、道-器、无-有、空-有、真-俗……名相虽多,结构相似,同属于“统一与杂多”结构群的一种开显。尽管成形的时间有所不同,这种结构性的相似性如此密集现世,就是体用论这一思维模式的丰硕成果。“体用”之名首出《易经》,之后经由大乘佛教、重玄道教尤其宋代理学数管齐下之后发扬光大,几乎照亮了后此东方文明史上所有的“杂多”问题。在体用论的观照下,现实的世界底层被认为有一根源性的统一原理,此统一的原理分散于现实世界的杂多的面相当中。万物的构成无不体现为统一与杂多的组合。
宋代理学的崛起之所以影响深远,乃为唐末五代十国之乱的创深痛巨,刺激一代儒者奋发图强,北宋士大夫文集中最常出现的基调,就是对于这一时期人伦荡然、礼崩乐坏的强烈反感。不仅政治社会秩序崩盘,似乎人间一切秩序都走了样,甚至连文字的表现都不对了。宋儒经过一番清算,得出结论,世界的秩序全盘错乱乃是佛老介入人间的秩序所致。而一旦关心的层面到达一切秩序、亦即一切法的层面时,议题性质会自然由经验的变为超验的。“天道性命”诉求于此跃上文化舞台,可以说本身就是文化问题的激发而至。重新建立儒家性命之学,成了理学家主要的共同的关怀。
无论基于佛道挑战还是其他原因,宋代理学均在渴望给人的主体及世界存在一个稳定而有规范性的基础。与汉唐儒家基于气化宇宙论与气化人性论的建构不同,虽然同样一并关怀形上与文化领域,宋代理学却转换了形上关怀的理论基础。一心要和佛老擅长的心性形上学争夺天下的理学家认为,前儒素朴的自然主义经解未能脱落桶底,儒学修养论变成了以自我本性的体认作为最高目的。虽然伦理与文化的层面并未废置,却被认为要呈现出厚度,儒者在此世的奋斗一举变成承体起用的立体的事业。宋明儒学的主流,无论周、张、二程、朱、陆、陈、王,他们具体的学说立论并非没有分歧、甚至有很大的分歧,却毫无例外的共享着这样的宇宙论与人性论:全体大用的世界观,逆觉复性的超越型人格,以及天道性命相贯通。这里有“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也有主敬-主静的工夫论。
某种程度,笔者本人其实也算是这一世界观的信奉者,笔者并不怀疑“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命题有体验的依据。但这类高明悠远的立论,对于经过各种现代性运动洗刷几过的今人,尤其没有相当的思想史训练者,并不见得容易进入。道如何具体的落在人伦日用之间?如果有另外一种介入路向,即通过气化的、交感的主体来建构一种伦际的伦理学,未必见得就更没有现实的、经验的意义。这其实也是近世东亚拒绝接受体用论思维模式的儒者最常采用的策略:追求从当下的道德意识出发,更重视或只凸显现实的纯粹的经验--但“经验”实在是与“自然”一样难以笃定的表诠:对于不同的生命状态,此之以为超验的,却可能是彼之已经经验的。
相偶论在国史上最鲜明的论述,当属学官两亨的清人阮元(1764-1849)的相关言论。几乎同时的韩国的丁若镛(茶山,1762-1836)则是异域一支劲旅。相偶论对儒家道德当建立于伦理关系之上、亦即建立于人与人之间一种合宜的行为模式之上的强调,在被理学主控了五百余年的思想界,可谓令人耳目一新、甚至震耳发聩。“相人偶”本是汉代俗语,清儒的这次回归汉学难得的超逾了语言学。在相偶论的视域当中,阮元重解“仁”说,认为如果离开人与人之间谈道德,不管其学下沉到心性深处、还是超越到形上理境,都无德可言。某种程度,这与整体清代学术重所谓“实学”,是有一体两面之功的,甚至竟也带上了些朴素的近代风味,例如相偶论对于经验性、分殊性的重视,对于普遍性的拒绝。我们不难从诸多西方思想家例如列维纳斯(1906-1995)的“他者”理论那里感受到某种相契。仁是需要在人间落实的。如何经由感通之力,汇通人我、物我,视角轮转,主体实现“脱己”(ecstasy),与他者时相互动,这一思路本身,即含纳了一种絜矩的成效。杨儒宾教授在另外的研究中,甚至认为:
18世纪相偶论的主张常被放在反理学的脉络下定位,但此说的价值可以提得更高,它可以放在生活世界的伦理意识立论,也可从理学的“一故神、两故化”或“太极-阴阳的诡谲同一”之说导出,《易经》可视为总教教门。(《情归何处:晚明情性思想的解读》)
只是,近世东亚这一波相偶论学者,对于心性深处与超越理境的严厉拒绝,确实没有多少道理。相偶论的人性只保留了气化的有限的人性、拒绝了超越的无限的人性,直接反对理学传统中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对分,认为这些都是儒学价值结构中的违章建筑、冒牌佛老。虽然相偶论学者也并非不讲究主体的转化、成德的路径,但这转化是就气质而行美化、强化、知识化,是“文”的学问,一般不存在临门一脚的质变的意识飞跃乃至超意识存在。这在体用论学者看来不仅过于浮浅、而且又把世界从立体拉回了扁平。相偶论学者一般都对形上学深怀忧虑,担心儒者在追求形上真实的路上忘掉对人伦道德最基本的关怀。但假如中国体验哲学并不存在后物理学意义的meta-physics,而更多指向meta-psychophysiology,形下与形上乃是通过气化主体在一气连绵中展开、以完成对“形气主体”的转化,则“相偶”没有理由不上通“本体”。
如果只是单纯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包括理学,那确实是不会有生命力的。道德需要真实有效的生命转化。百余年来流行至今的“吃人的礼教”之类说辞,固然因为经学断灭之后几代国人再也进不去传统的世界观与人性论,但也不可能完全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先于阮元的戴震(1724-1777)的“以理杀人”说已着其先鞭。彼时儒学的现实的表现,恐怕还是出了不少问题。如果把清学、特别是主要以语言学的方式回归“汉学”的清学,视为古典的全貌与正宗,毋宁是走板荒腔的古典--新文化运动一代闻人反抗的,未尝不包括这个非驴非马的东西。人伦之际、乃至天人之际的合理如实的关系,都需要通过有效的真实的沟通,才能成为现实的可能。不断气化生成的相偶主体不仅要与天道义理共振、同时也必然与社会规范、风俗传统共振,如此形成的人际、人类社会,才可能具有寻求多元、平视他者的当代性的合理因子,才可能是如实紧密相依的共同体,而非勉为其难的道德捆绑、言不由衷的规范要求。相偶既然意味着伦理的关键乃在对偶的双方身上,是在包含双方在内的场域中发生,相偶也就一定意味着全方位的感通。儒家从周公、孔子以下,都坚持对伦理世界与文化世界的肯定,即使理学范围内亦概莫能外。这里不仅有诗书礼乐、孔孟之言作为经典的保障。如果良知总是要在人伦之间展开,如果《易经》所言乾坤并建、双元同一之说具有存有论的优先性,有一必有对,无独必有对,则相偶论特重人的气性、特重人际间道德情感的优先性就非常值得重视。这样的新诠六经、重解圣人,毋宁可以视为是对儒家伦理极大的肯定。伦理的活化与价值的扩充为每个具体时代、具体时空所必须,相偶论的交互性决定了其本身一定处于不断的气化生成之中,对于追求“扣其两端而择其中”而不要流于“执一”固理的木强僵硬,实有天然生动的警戒作用与治愈功能。当然同时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如果一味沉湎而执情,反而一定会堵塞可以感通的管道,使得相偶成为不可能。如果一味流于情识的炽热至极,反而一定会烧毁期待于偶合中成全人格的初衷与目标。
相偶论容易给人留下现象学的印象,但相偶的层次有深有浅,理想的相偶仍然有待工夫的证成。对偶性与绝对性、人情性与超越性、乃至伦理性与道德性,在气化生成、阴阳互动的格局之下,完全没有可能是孤阴孤阳、势不两立。和杨著中的结论类似,笔者也相信相偶论是必要的,这很可能是一种典型的渐教法门,而且和体用论之间更不是无法兼容的。某种程度,能明体达用之人,即是最适合相偶之人,反之亦然。以相偶性为基点,同样可以经由逆觉返证,最终契会那一切未尝分化而又创生不已的始源之处。体用论可以是相偶论的完成,相偶论可以是体用论的基础。这是不脱相偶的体用,照见体用的相偶。真正的体征悟觉者也恰恰不会遁世逃避,天下一家的伦理情感不是无中生有、不是将无做用,而是冥契一体同流之后的不容自已。就此而言,任何体用的如实开显必然是相偶的,任何相偶的深层回溯也必然是体用的。让体用和相偶成为有情世界的十字打开的彼此支撑,可能是一种更允当更契机的选择。“即阴阳证太极”,本体总是以对偶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本体在对偶中依然维持其自身的超越性。无论儒学还是理学,其高阶力道,都必然是解行并进的。陆王并非程朱的对反,更是程朱的完成。真正的道德在于人间性,亦在于超越性,两者相辅相成,而非势不两立。真正的相偶论,或者说完成的相偶论,其伦际并非止于人际、同时必然朝向天人之际。横摄与纵观十字打开。在实际存在的秩序中,本体从来没有超越阴阳对偶,始终都是太极在阴阳中、本体在对偶中,“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正蒙·太和》),这种即体即用的体用观,日后即被熊十力视为中国本有而非受佛道影响的体用论。
相偶论虽然与体用论立论的基础看似相差很远,如果换一角度,它们之间的距离实际又很近,它们同属于主体哲学。一种交感、互渗的主体,为传统中国的道德哲学共同必须。理学家与反理学的儒者显然分属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后者虽然尚有意识哲学的意涵,却并不隶属“心学”。但这两种类型并非是绝对断裂的。能够链接他们成为一种上升的不同阶段的,乃是气化主体。
二 气化论与制度论
气化论是先秦至于汉唐宇宙论与人性论的大宗。宋代理学家中,张载最为重气,因此也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对分的表法。但最为特出的理气论,仍然是朱熹提出的。相较于理学、心学的提法,气学的系谱图像显得更为模糊,直到晚近,相关研究才倾向于更精细的区分,例如刘又铭先生的“本色气论派”与“神圣气论派”、马渊昌也先生的“理学的气论”“心学的气论”“气学的气论”等。杨著是书中则将其区分为先天型气学与后天型气学,用来指称超越型气学与经验型(自然义)气学。
因为气化生成,才使得体用论和相偶论成为可能,也使得体用论和相偶论的链接成为可能。虽然前者气化生成的方向更强调纵贯,后者气化生成的方面更强调横摄,而且因此使得同样强调气化生成的儒家学派再次割裂为二。杨著勾勒两种气学,先天型气学以张载、刘宗周、罗钦顺为代表,他们无不同属理学队伍中的重镇,却以气化精微,调整并弥补了朱子学说中理气二分的不足;后天型气学以王廷相、吴廷翰、高拱、陈确、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这支队伍尽管并非都有明确的相偶论认识,但他们对于有限人性论的认肯,倒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先天型气学仍是理学内部的精进版,后天型气学,才真正是反理学的立场。检测气学属于先天型还是后天型,观其所持人性论为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即可,就工夫论而言,则是是否支持“复性”说。先天型气学虽然也重物重气,却不是如后天型气学那样自然主义的用法,在先天气化的关照之下,“物”皆为道之体现,“气”皆为道之流行。
一旦涉及到气化的主体,就不可能不关涉到气化的宇宙。理学气化论(本体宇宙论)与汉唐气化论(气化宇宙论)最大的区别,仍在前者对于“第三极”(此即周敦颐《太极图说》对“无极而太极”的强调)的挺立或朗显,外化内不化、内即化即不化,其本质,仍是体用论的,故也是理学的。理学家队伍中精研气学者不少,他们通过气化学说建构更合理的体用关系,却绝不反对体用论,因此和那支反理学的气学队伍观点相差甚远。因为唯物论的流行与标签,这两支气学队伍的区别目前仍并不十分为学界所明朗,往往被粗疏的混为一谈。其间最好的检测标准,大抵就是工夫论:隶属理学的先天型气学均承认静坐是极好的辅助“通关”手段,反理学的后天型气学则毫无例外,听到“主静”就极无好感。对于先天型气学,逆觉复性足以加深、加大道德实践的动能;对于后天型气学,这种强挽分殊性的工夫却只能导致意识虚无化。朱子“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不二法门至此成了万箭穿心的靶的。后天型气学重视的是才气学习,拒绝了先天型气学的超越境的普遍性,而在主张通过气质之性的社会性扩充、体现经典或文化传统所赋予的统一价值的过程中,迈向了另外一种设想中的“整体性”。根本处言之,这是一种自然主义人性论的回归。后天型气学强烈地坚持:人性真正的内涵,只能是血气心知,而非天地之性;人性发展要向前、而非逆返,是积累、而非遮拨,是气性的强化,而非异质的转化;人性应该是社会性的全体化,而非超越性的一体化。先天型气学与后天型气学虽然都有对整全性的追求,但前者主张纵贯面(体用)的万物一体,后者主张水平面(横摄)的万物一体。后天型气学的出现当然并非毫无意义,其理路自此一说,也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但与先天性气学之间,要严加区分,二者离则双美、合则两伤。
反理学学者往往留给人关心人道、忽视天道的印象,但并不因此均成为制度论者。反理学的制度论者另有其人,这支铁骑即被称为制度论的儒学。与这队人马相较,体用论儒学与相偶论儒学确实应该属于主体哲学的同一阵营。但如果从更注重横摄的现实的人际关系入手,也可以说,制度论儒学与相偶论儒学则共享了一套武器,均强调应以经验入手,反对体用论儒学的超验性格。最早一波反理学的声浪,例如宋代的永嘉学派,便属于这一制度论阵营。杨著中没有专章展开的清人凌廷堪(1757-1809),也大体可以纳入。
叶适(1150-1223)的生命周期跨越两宋,是永嘉学派的杰出代表,观其生平起止(北宋亡于1127年),即不免令后人起悲怆之感,永嘉学派“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倡言,宁为无故哉?制度论儒学也反理学、反天道性命之说,但反的理由却不同于相偶论儒学。一般而言,制度论儒者同样喜欢自称返归六经而非论孟,他们往往认为子思、孟子之学对先王之道的引申过多、过犹不及。“致虚意多,实力少”是学宗思、孟的理学家的共罪(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在这派学者看来,儒家之道只能是人文世界的概念、是建立在礼乐制度上的规范系统,不能是心性论的语汇,更不能是形上学的语汇。他们对人性的信心往往不大,或者也对人性的论证没有兴趣。在主体的构造上,礼的秩序性优先于气的感通性。他们大抵也会抵触性善论,而对荀子更有好感。
像理学的建构那样,一旦将问题踏入宇宙论、人性论与价值观的领地,就难免于要在人的地步冒犯“超越”(超人)的世界,如此杳渺玄虚之言,何以服人服众呢?叶适就认定,人的本质就是礼乐人,也可以说就是政治人,没有“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纵贯型人格、只有“礼乐性命相融通”的横摄性人格。和相偶论类似,这种制度论的人性论与价值观,与其说是在复古,不如说,反而颇有近代意义:其所关怀的人,是在现实的制度中如何各得其所的社会人或政治人。这样的人格是建立在生物性-历史性-社会性基础上的人格,必然强调分殊性、而非普遍性。在这类学者看来,只有如此,方能使得儒道与佛道各就各位、各回老家--方能让儒学回归原初的儒学。
需要说明,制度论儒学和制度儒学并非一事。因为对于主体论儒学,无论心性论儒学还是相偶论儒学,其实都不可能拒绝政治,儒学的根本性格原本就是人间性的,可以说任何儒学都是制度儒学,区别只在制度的基础设计例如宇宙论与人性论的安排有所不同。因此,制度论哲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儒学,制度论儒学的指标项特征,仍然是同样拒绝体用论的思维模式。
结论
理学与反理学两股儒学思潮,在各自的时空当中,都真诚地认为自身重现了原始儒家(真儒)的价值,然而,是否不如说,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随缘应机中,开显并丰满了儒学的意义光谱呢?意义可以异议。经得起异议的意义才是真意义。
儒学的人间性格极强,对于人伦安排与文化秩序有根源性的关怀,因此,倾向主体哲学的体用论和相偶论,与制度论儒学之间也不应该是无法沟通的。毋宁说,在追求共同的意义之维的途路上,它们属于不同的阶段、而非不同的方向。“礼”(制度)的成立不可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感通相偶永远是必要的,是基础更是完成:主体的本性乃是超出主体,而且需要与作为他者的主体面相与之配合,主体的性格才可完成。
所彰古学不同,自然源于所见之道不同。然而如何认定自身所见之道是局部还是全体呢?理学与反理学这场滔滔不绝的千年争执,大抵早在孟荀之辨,问题已经出现:道德--笔者更愿意称为的意义,道德是要建立在道德情感-道德之气-性天交界之处呢?还是要从仁-礼之间、尽伦尽制之间取得合法性?道德是要主体精之又精、深之又深,将“人”的成分稀释到极点、与绝对睹面相对?还是要主体在语言、性别、历史、制度的交界处批判被批判,来回折磨?钟泰先生尝以“实际效果论”来概括孟荀之间无以分正负高下的“善恶”性论:“于孟子而得性善,则君子有不敢以自诿者矣;于荀子而得性恶,则君子有不敢以自恃者也。天下之言,有相反而实相成者,若孟、荀之论性是也。”孟子持性善论,旨在强调人道德生活的先天合理性、从人内心开辟出价值之源,更重视个人精神;荀子持性恶论,同时又凸显“知虑材性”,则同时强调了人之道德教化的先天可能性与后天必要性。
孟内荀外的生活是否可能呢?“天道性命相通”与“人伦礼乐(制度)相通”是否有更好的结合方式?笔者相信有。例如不是从正统-异端、而是从圆满-偏至的角度看待问题。但后一种说法显然仍然难免要暗含了判教之意,难免仍然要与主体的构成有相当的联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落脚居然仍然是“工夫论”的问题。我们的立论仍然如此受制于我们的“经验”,是否经验过“超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或者说,在恰切的时空,人性应该选择有限的表现,还是冲向无限的挑战。无限的人性论仅仅是种理论设计吗?面对往古来今遍布各大教门与学门的密如胡麻的证道经验,我们很难、也没有资格如此定论。虽然无限性的知识该如何敞开,包括时节因缘的具体限定,确实是需要审慎斟酌的。
最后要说的是,杨儒宾教授不仅思想史的功力深厚稳健,因其才情富赡、娓娓能书,故在问题意识明确、结构体大思精之外,其书行文典雅温厚而又妙趣横生,可以令笔者这种理工科出身缺乏古典学训练的读者进入哲人之境都并不觉得辛苦,反而兴味盎然,精神操练可以如此愉悦,实在是人生很大的福报。原来学术史的写作也可以如此生动、平实、圆融。只是笔者的古学修养实在有限,故这篇书评虽然几经努力,却很难说充分表现出了杨教授之学万一,无论理解还是表达,均远不能如原著的周全、缜密、恰切。
作者:秦燕春,始修医学,后治文史,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古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着有《诗教与情教:新文化运动别裁》、《思复堂遗诗》笺注本、《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袁氏左右》、《青瓷红釉》、《问茶》、《历史的重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