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范畴是一个宇宙论概念,而朱熹《太极图解》的“太极”范畴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太极”这个词语来自《易传》,虽然也是宇宙论概念,却不同于周敦颐的宇宙论。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宇宙论,都是存在者化的观念,因而都面临着当代哲学之前沿思想的解构。因此,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来说,如果仍要使用“太极”“无极”这样的词语,那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解构、还原而重构。具体来说,“太极”作为形上的“存在者”,即是一个存在者化的观念,因而有待于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为之奠基;“无极”亦然,它应当被改造为一个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
众所周知,对于宋明理学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具有“开山”的地位。方旭东教授在法国出版的专著《周敦颐太极图讲记》(以下简称《讲记》)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最新研究成果。
如果仅仅从书名看,《讲记》所研究的似乎不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是《太极图》。从学术范畴讲,《太极图》属于“易图”的领域。据我孤陋寡闻所知,目前研究易图的最渊博的专家,应该是郭彧。他送过一本书给我,是与李申合编的《周易图说总汇》;另外,他本人还出版了《周易图像集解》和《易图讲座》等专著。关于周敦颐,他也有专题论文《〈周氏太极图〉原图考》。我看了《讲记》的参考文献,没有提到郭彧的著述,只列出了李申的《易图考》。就我本人来说,遗憾的是,郭彧以及其他易图专家的著作,我没有认真研读过;原因是我对“易图”没有学术兴趣。
但是,从实际内容看,《讲记》的研究对象,虽然围绕着《太极图》展开,而实际上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太极图解》。不仅如此,此书真正关注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尤其是朱熹“太极”范畴的内涵及其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为此,此书特附了一篇专题论文《太极果非重要乎?》。说实话,日本学者山井涌竟然提出“‘太极’在朱熹哲学中是否重要”的问题,陈荣捷等人居然煞有介事、正经八百地与之辩驳,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太极”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无需争辩。《讲记》也说,“太极问题涉及宋明理学诸多关节,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朱熹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讨论“易图”的问题。再者,我不打算讨论文献“考据”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对作为易图的《太极图》没有专门的文献考据研究,而且感觉《讲记》的考据是颇为扎实的。我只讨论一些“义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哲学”的问题,并且主要集中于“太极”以及“无极”范畴的问题,这也算是对方旭东教授提出的“太极果非重要乎”问题的一种回应。
一、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范畴
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原本,首句究竟是不是朱熹确定的“无极而太极”,这个朱陆之辩,其实是一个无法考定的公案,这里不去讨论它。我赞同《讲记》的这个态度:“应该放弃对唯一确定‘真本’的过度追求,而去揭示不同版本的‘敘事’的生成过程。” 这是一种符合当代诠释学立场的态度。
至于“太极”与“无极”的关系,朱熹说:“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这个理解,我觉得大致是符合周敦颐的原意的,因为“太极”无疑是“本”,而周敦颐既说“无极而太极”,又说“太极本无极也”,即同时称“无极”为“本”。可见在周敦颐这里,“太极”和“无极”所指称的是同一个东西。
问题在于:这个“本”,究竟是本体论(ontology)的概念,还是宇宙论(cosmology)的概念?这需要看看周敦颐如何谈“本”。但是,除“太极本无极”一句以外,《太极图说》再无“本”字。周敦颐谈论“本”比较多的是《通书》,值得考察一番。其中有的“本”既非本体论意义的,亦非宇宙论意义的,例如“乐者,本乎政也”,显然不在我们这里的考察范围之内。
稍加考查,不难看出,《通书》所谓“本”,就是“诚”。他说:“诚,五常之本”;“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故思者,圣功之本”;“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 但这里的“诚”之为“本”,并不只是宇宙之“本”,而是“圣功之本”。所以周敦颐才会说:“天下之众,本在一人”;“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太极图说》以“太极”“无极”为“本”,但并没有提到“诚”,即看不出“太极”与“诚”的关系;而《通书》则大谈“诚”,但是,尽管有一处提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却同样看不出“诚”与“太极”的关系。明确地将周敦颐的“太极”与“诚”联系在一起,是朱熹的诠释。
此外,正如《太极图说》一样,《通书》也只有一处提到“本”与“太极”的关系,即:“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这里的“本则一”显然就是《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这里的“二本则一”并不是说“二气”或“二实”(即阴阳)是“二本”,而是说阴阳虽为“二”,然而“本则一”,这个“一”就是“无极而太极”。但这里周敦颐仍然没有涉及它与“诚”的关系。
归纳起来,可以说:周敦颐尽管将《太极图说》的“太极”或“无极”和《通书》的“诚”都称为“本”,但他所谓“本”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内涵,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太极图说》的“本”是一个宇宙论范畴;而《通书》的“本”则具有本体论的意味,唯其如此,它才能开出宋明理学的本体论范式。
因此,我同意《讲记》将周敦颐哲学归属于“宇宙论”这个判断。作者指出:“周敦颐《太极图》《太极图说》所要表述的主要还是一种宇宙论学说,而朱子的《太极解义》则自觉地将‘太极’作为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周敦颐是要在《太极图》中把中国宇宙论的三大模式融合”;而“朱子成功地把周敦颐的太极学说改造为一个本体论敘述,真正确立了太极的本体地位”。这样看来,作者确实抓住了周朱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但同时,《讲记》有时又将周敦颐的“太极”称为“太极本体”、“太极之本体”,这就出现了混淆、矛盾。
二、朱熹《太极图解》的“太极”范畴
关于宇宙论,《讲记》作者归纳道:
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第一,基督教神学的神创论,世界由一个处于世界之外的“第一推动者”创造;第二,以《太极图》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世界无需外部存在,仅凭自身就能够自我生成;第三,以《物种起源》为代表的进化论,生物由无机物而来,人类从单细胞生物经过亿万年进化而来,近于“无中生有”之说。
这个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宇宙论”是一个哲学(包括宗教哲学)概念。因此,与之相对的概念不是科学的“宇宙论”,而是哲学的“本体论”。大致来说,人类知识的发展,曾经是哲学与科学不分;后来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于是,哲学中的宇宙论模式宣告终结;换言之,自此以后,对于哲学来说,宇宙论模式不再是有意义的思维,它对宇宙起源及其演化的说法基本属于“胡说”;科学的“cosmology”应当译为“宇宙学”。当然,不可否认,在近代的科学宇宙论之前,哲学宇宙论的探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是人类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对宇宙万物的总体知识的一种根本统摄。
真正的本体论与哲学宇宙论的根本区别是:其一,“本体”(noumenon)所指的并非任何意义的有形实体(substance)(宋明理学的“本体”概念亦然);其二,并不存在从本体到万物的时空意义的演化(evolution);其三,与“本体”相对的范畴并不是“万物”,而是“现象”(phenomenon)。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较之“本末”模式,“体用”模式更接近本体论。
现在来看朱熹《太极图解》的“太极”概念。首先必须意识到:朱熹对“太极”的理解,与周敦颐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讲记》指出:朱熹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实是为了“证成他自己的哲学”;所以,他“主要以理校法,即按逻辑和义理来论定是非”。 这里的“理校”所依据的“义理”,当然是朱熹自己的理学思想的“理”概念,而不是周敦颐的“理”概念。因此,绝不能像《讲记》所说,“我们可以根据朱子《太极图解》的文字及其包含的义理去推定正确的图该当如何”;换言之,根据朱熹的诠释去推定周敦颐的哲学思想,这是不能成立的。这暴露出《讲记》的另外一个矛盾。
因此,关于“太极”,正如《讲记》所说:“围绕‘极’字……朱子则采用了创造性的诠释,展示了他身为哲学家的理论抱负。” 但是《讲记》又说“心学、理学的一般风格和它们各自的经典诠释方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还说“朱子的《太极图解》《太极如说解》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太极图说》存在互文关系”,这就自相矛盾了。其实,朱熹对周敦颐“太极”进行“经典诠释”,所依据的正是他自己的理学的“一般风格”,而不是周敦颐的“风格”。
例如周敦颐《通书》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 朱熹对此的理解,《讲记》进行了很好的概括:
朱子关于“五殊二实”的表述,应当这样理解:因为太极是“本”,且只有一个,所以称之为“一本”。“五行”的数字为“五”,“五”比“一”多,对应于“理一分殊”的“殊”,因此“五行”被称为“五殊”;阴阳为数有二,“二”既不是“殊”,也不是“一”,朱子另想了一个词“实”来称呼,就是所谓“二实”,“二实”即“二元”。
然而,朱熹是用“理一分殊”来解释。这当然不是《讲记》首倡,例如已有学者说过,“《太极图说》与《四书》道统分别侧重道统本体向度和工夫向度,二者可谓源流关系,理一分殊关系”。但众所周知,“理一分殊”并不是周敦颐的思想,而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发展关系。这里最根本的区别是:“理一分殊”并不是宇宙论的模式,而是本体论的模式。
鉴于“太极”一语出自《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因此,朱熹对“太极”的理解,应当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标准: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
显然,按朱熹的理解,“太极”就是“理”。但是,这并非周敦颐的思想。
此外,按《讲记》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是:“太极是‘本’,且只有一个,所以称之为‘一本’”;这个“一本”就是“理一”。然而,作者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有非常强的把宇宙生成归到‘气’的倾向”;而“朱子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气论’、‘气本论’一转而为“理论”、‘理本论’”。 这样一来,朱周之间的分别就是理本论和气本论的区别了。但是,周敦颐的思想能不用归结为气本论,却是一个大可商榷的问题。
三、《易传》的“太极”范畴
周敦颐和朱熹以及整个宋明理学的“太极”,都出自《易传》。但应当指出的是:帝制儒学后期的宋明理学的“太极”概念,不仅不同于以《周易正义》为代表的帝制儒学前期的“太极”概念,更不同于《易传》本身的“太极”概念;它们属于不同时代的哲学范式。为此,有必要来看看《易传》的“太极”概念,这是“哲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易传》原文如下: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wěi)者,莫大乎蓍龟……
王弼注:“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孔颖达疏,按照“疏不破注”的原则,只是在王弼注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但是,王弼及孔颖达的诠释,属于帝制儒学前期的哲学范式,即它既不同于帝制儒学后期的理学,也不同于属于轴心时代哲学范式的《易传》。简要分析如下:
首句“易有太极”之“易”,乃至整部《易传》之“易”,都有两层含义:有时是不带有书名号的“易”,有时是带有书名号的《易》;后者是对前者的效法,即“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从上述引文看,首句之“易”应当是加书名号的《易》,所以紧接着才讲单爻的卦画“两仪”(
 )、三爻的卦画“八卦”(
)、三爻的卦画“八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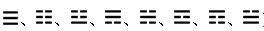 )。至于“四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应是两爻的卦画
)。至于“四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应是两爻的卦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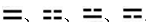 。
。
但是,这样一来,“太极”就会没有着落,即不存在这样的卦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太极就是阴阳、阴阳就是太极;但是,“是(太极)生两仪”之“生”就讲不通。“生”显然就是一个宇宙论的概念。
所以,“太极”并不属于带有书名号的《易》,而是不带书名号的“易”,即指易道本身。这也就是下文所说的“法象”,即《易》乃是对“易”的效法,诸如“两仪”是效法“天地”、“四象”是效法“四时”,等等。于是,“太极”显然就是天地未分的原初状态,即它不是“二”,而是“一”。这个“一”,就是一个形上的存在者。
不仅如此,实际上,“太极”作为“法象”“效法”的观念,更直观的取象乃是“建房”。这是因为:“太”就是“大”,上古乃是同一个字,故《说文解字》无“太”字(徐铉误以为“泰”字的古文为“太”);“极”即栋梁,即《说文解字》所说的“极,栋也”,段玉裁注“极者,谓屋至高之处”,“今俗语皆呼栋为梁也”,“引伸之义,凡至高至远皆谓之极”。所谓“太极”,就是房屋的那条最高的大梁。这是中国人建房的传统,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仪式,相当于今天西方传入的“奠基”仪式,叫作“上梁”,古人称之为“立极”。它被赋予哲学上的象征意义,也叫“立极”,又叫“建极”:宇宙的最高本体,就是“太极”;人间的最高权力,就是“皇极”;人道的最高原则,则是周敦颐《太极图说》讲的“人极”。
这其实是中西相通的形而上学观念,中国哲学谓之“立极”,西方哲学谓之“奠基”,两者都是建房的第一仪式。但中国哲学的“立极”观念是自上而下的,从最高的大梁开始;而西方哲学的“奠基”观念是自下而上的,从最低的地基开始。
更根本的区别是:西方的“奠基”不是宇宙论的观念,而是本体论的观念。西方“奠基”观念始于康德,他说:“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 后来胡塞尔(Edmund Husserl)明确地给出了“奠基”的定义:“如果一个α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 注意:这里所说的并非宇宙论模式的那种时空经验上的优先性,或逻辑前提上的优先性,而是“存在”上的优先性。 这显然就是一个本体论观念。
然而《易传》的“太极”却是时空经验上的优先性。由此可见,《易传》的“太极”并非朱熹理学的本体论范式,而是一种宇宙论范式。不仅如此,《易传》这种宇宙论范式也不同于周敦颐的宇宙论范式,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就不展开了。
四、“太极”观念的当代哲学省思
以上三节,都属于“哲学史”的话题;现在谈谈“哲学”的问题,即: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发展来说,“太极”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当然,这已经超出了《讲记》的论题,因为作者的意旨并不是对“太极”进行当代哲学的省思。
前引王弼注《易传》说:“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紧接着,孔颖达引何氏之说:“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极’,太极即无也”;“下篇明幾,从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 这是将“太极”视为“无”,明显来自《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太极”范畴的本体论化,尽管《老子》之所谓“无”未必是一个本体论概念。
这里的问题是:何谓“无”?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所谓“无”都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类观念:
一类是标志某种“存在者”的“无”观念,即指形上存在者,即《易传》所谓“形而上者”。形上存在者,包括“太极”,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无”,并不是说它“空无”,而只是说它的内涵尚未展开。唯其如此,它是不可定义的。西方哲学亦然,例如黑格尔所说的“纯有即无”,即:“开端就是纯有”;然而由于这个“有、纯有,——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因此,“有、这个无规定性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 这个“纯有”即“无”,实际上指黑格尔那里的那个内在规定性尚未展开的“绝对观念”,而它“正是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存在者整体”。这倒类似于朱熹对“太极”与“无极”的理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这就是说,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太极”谓其至高无上,而“无极”则谓其尚未展开。总之,“太极”是一个存在者观念。
而另一类则是标志“存在”的“无”观念。它之所谓为“无”,同样不可定义,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内涵尚未展开的形上存在者,而是说它根本不是任何“存在者”,而是“前存在者”的“存在”。这涉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的“存在论区分”(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即“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尽管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Being)观念还有“不彻底性” ,但这个区分是十分重要的,超越了轴心时代以来的本体论形上学传统。宋明理学不承认这种意义的“无”,是因为他们还不具有“存在论区分”的观念。张载就是一个典型,他说:“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知太虚即气,则无无”。
然而,按照“存在论区分”的当代哲学思想观念,那么,不论是宇宙论模式还是本体论模式的“太极”和“无极”观念,都是应当予以解构的。当然,所谓“解构”( deconstruction)并不是简单化的抛弃,而是由“还原”而“重构”。
据此,前引《讲记》所说的“以《太极图》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世界无需外部存在,仅凭自身就能够自我生成”,而且并非“无中生有”,即属于上述第一类“太极”观念,也就是形上存在者的观念。这里,《讲记》存在着两点值得商榷的观念:一是没有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二是简单地否定了“存在即无”的观念。
由此可见,对于当代及未来的中国哲学来说,如果仍然要使用“太极”这个词语,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它是一个“形而上者”、存在者化的概念,即是一个有待奠基的观念。前面说过,康德最早提出“奠基”观念;胡塞尔则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但胡塞尔的“奠基”观念还是存在者化的,他那里的原初的终极奠基者是某种绝对主体的纯粹先验意识的意向性(Noesis)。海德格尔才突破这种存在者化的“奠基”观念,即以“基础存在论”来为传统本体论奠基。当然,他的“奠基”观念仍然是不够彻底的,因为他实际上是用“此在”(Dasein)的生存来为一切奠基,然而“此在是一种存在者”。
同时,假如仍然要使用“无极”这个词语,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如果说“太极”所指的是作为“有”的“形上存在者”,那么,“无极”所指的就应当是作为“无”的“存在”。这就必须放弃周敦颐和朱熹“无极而太极”的观念,即必须明确“无极”与“太极”不是一回事。用《老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说法,那么,“万物”是众多的形下存在者;“有”是唯一的形上存在者,即“太极”;而“无”则是前存在者的存在,即“无极”。